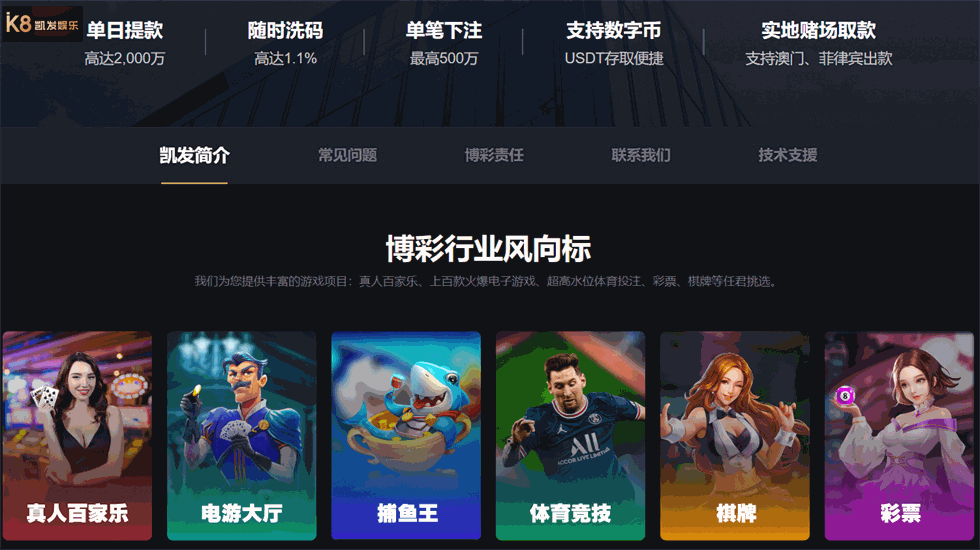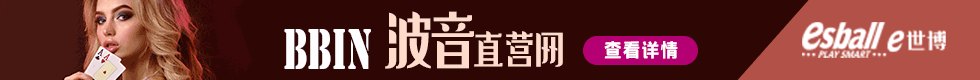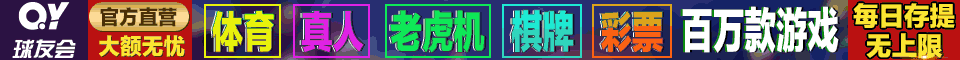木牌你是我痛苦的信仰
发布日期:2022-01-06 18:45 点击次数:120
《木牌,你是我痛苦的信仰》
2018年夏,湘江的风吹散了日落,少年坐在江边勾勒着明天。
5月13,长沙,我抛下新买的变速车和挂科的科三,揣着五百元钱,崭新的护照、几件衣服走向高铁站,我忘乎所以,仿佛远方有我的爱人。
14日下午,木牌步行街,阳光刺眼,天空荒凉,地面肮脏,新开张的商场挂满彩旗,一派农贸市场的喧哗。我在陌生和不安中,下车,跟着带我的HR,在村中彳亍着。村,歪曲的小街,拥挤的小店,水果、零食摆在外面。穿过林立的赌场,我们停在了五层宿舍楼的门口,我拧着箱子跟着他继续上楼,转角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只”延安“:"既然来了,岗位也很轻松,不会的好好学,你年纪小学得快。“ 我把双肩包跨到肩上,接过烟:”第一次接触这个,不知道靠谱吗,不会被祭吧。“ 火机的咔擦声在吵闹的楼道里迅速被埋没。四层楼道往里的第二间,我跟着他走进去,开门,破旧的床架、随地的烟头、木板在床架的支撑下显得越发艰难。“你先把东西放下,等下给你送生活用品来,今天休息,明天再办入职,护照先给我,到时候公司要办签证。”他靠在尽头的窗台指着空床说。我从包里找出护照递给他:”好,谢谢,这里有WiFi吗“。 ”有,你打开就能连,我晚上下班了再带你去办手机卡,我用的是S卡信号好。”他一边走下楼一边告诉我他要去公司,让我先呆着。
这里是做外卖,小生意者的天堂。宿舍的一、二层住着本地人,他们大多是来自其他省的打工仔、农民还有摩托车司机。旁边蓝棚子下的小店从下午到凌晨一直热气腾腾,2美的炒面最多人吃,中国人、本地人、打工者、农民、嘟嘟车司机。脏水泼向门前路口的马路,对面按摩店的小姐姐向我招手:“按摩啊,按摩..”。我低着头闪开,回到宿舍。陌生和未知,常常让人感到失落。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熟悉,我站在窗台望向下面,发现了一家中国超市,我走着下楼,打算换点美金,去最近店吃点东西。换好美金,吃完东西我走回宿舍,开门遇见了小苏,南京人,个子高高很阳光。他正放下背包和行李箱:“哥们,你好,刚从国内过来吗?我也是”。他抄着不标准的普通话勉强的笑着:“昂,朋友在这边,过来混几天“。一旁的HR是他的朋友,很快我们玩到了一起。
柬越边境小镇的夜晚更让人心慌,木牌小镇的小巷灯火闪烁。在人事的热情邀请,我和小苏、HR一起在整条越南街找了一家躺了下来,喧闹的店里,帘子隔开了整个世界,嬉闹声声不听的夹杂在空气中告诉每一个人 。他们会问起女孩的出生、年龄、家庭情况,当然还有出台价格。我没有心思听这些,躺在垫子上发呆,任由小姐姐捉弄。我究竟是怎么样不会想到在异国的他乡,我遇到的竟是这般风景,却也尚好,大概整个世界我与你们都是同样的人。
雨季的东南亚格外凉爽,小雨伴随着风袭来。她们迎着“五月的风沙”站在门口张望,像只被解放了的惴惴不安的精灵。
不论在怎样的夜,我总是会想起明天该怎么去生活,怎么去对待这个世界。HR告诉我,明天会带我办入职,十二点一刻我便入睡,枕着希望,盼望着明天。
小苏的咳嗽声打乱了我的梦乡,手机里的北京时间是四点,我望着漆黑一片:“小苏,怎么喝这么多,我箱子上有水,你拿着喝口水。”回应我的只是一片寂静的午夜传来的一阵阵喘息声。宿舍不隔音!我惊奇地竖着耳朵聆听着。两个孤单的灵魂,在远方欢愉着,小镇充满着诱惑。我点了烟,站在窗子前,周围尽是高低不等的小房子和明明灭灭的灯火,近处的巷子,远处的大街,一个偌大的布满生灵和肮脏的远城村,也许十六世纪的伦敦就是这个样子。
阳光认真的照到了床尾,明媚的夏日。我把微信的消息发送了过去,HR带我办了入职。
“怎么样,累不累。给,欠我一美金”小苏下班后回来提着两个椰子递给我一个。我接过来递给小苏一根七星:“一美金,你这不是坑我吗,工作慢慢来,慢慢学,总会过去的。”宿舍停水,我们便提着桶去楼下接水。“我可能要回去了“他说。我望着他呵斥道:”什么玩意儿,这才几天就扛不住了,有意思吗,这么折腾。“深夜,我喜欢和他买鸭货、鸡爪,坐在窗子前喝椰子,也偶尔喝吴哥啤酒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家里有事,母亲卧病在床。从那之后,我经常一个人在深夜回宿舍,到了四楼,还得经过很长一条过道,才能走到自己最靠边的宿舍。拿起钥匙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,害怕隔壁房子的邻居突然冲出来。说是邻居,其实是一堆人,隔壁房子貌似是一家公司的员工宿舍,而且都是清一色的花臂男,有一次那个大门开着的时候,偶然看见过里面很多个上下铺的床,堆满行李跟杂货,还有横七竖八的酒瓶,散落一地的花生米以及被嚼得稀巴烂的毛豆。楼道的灯光很微弱,有时候需要很用力地跺脚才能声控亮灯,不敢叫出声来,害怕影响别人,更是害怕招惹别人。月休的时候想着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,打开冰箱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,饥肠辘辘昏天暗地,实在是没力气再走到很远的超市或菜市场买菜,于是开始叫外卖,一般两个菜的价钱才达到起送的条件,于是只能吃完一个菜,留一个菜到晚上吃。
有一次我在夜里惊醒,想起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人陪着一起吹牛皮、喝椰汁。我拨通了小苏的视频,视频后的他叼着烟还在长沙的大排档喝着啤酒:“想我没!我可能永远不会来木牌了,新闻看了吗,中柬联合行动,西港大军都撤了。“ 我望着明灭的灯火下的街道少了些人,我说:“看到了,你也别过来了,我先干着吧,薪水不低了。“他又说:“木牌也不安全,指不定哪天呢。”“时间久了,不大喜欢回家,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动力。“我苦笑着叹道。一阵寒暄过后,我们彼此挂断了视频。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明白,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的人,在脆弱的午夜里,都会安慰对方。
在木牌的第一年里我过的很艰难,不敢买水果吃,因为没多少钱。最大的乐趣,就是下班了,买点零食回来看电影、追剧。
天气好的时候,会一大早起床,拆开床上的被套,把被褥拿去阳台,拎一把椅子出来,被褥就搁上面晒了,然后把换下来的脏被单浸泡半小时,再来回揉搓,过水清洗,宿舍没有洗衣机,于是要把洗好的被单放在桶里,先把一头的水拧干了,再换另一头拧干,然后用一家支在阳台。我一度感觉这种安静的状态很是恐慌,我尽量还是强迫自己和室友有说有笑的生活着。
年后,我们换了新宿舍,条件变得很好了,公寓酒店型的,三人间。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认识了很多越南人、本地人、商店老板、摩托车司机。他们在不远的距离只收我一美金的车费、在后来我不喜欢公司免费发放的生活用品的情况下,有一次我经常去本地商店购买的一款类似香港的牙膏时,我问起了他最近的生意是不是又变好了,他告诉我,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他又说前几天几个中国人偷他店里的美金,没有抓到。因为我们熟悉,我还是习惯性的反驳他:”你确定是中国人吗?你是不是又看错了。“他没有细说,只是在我走的时候告诉我:“我们不是看不起中国人,只是没什么好感。你们这些人,带着青春和才华,带着势利和手段,来到这里追求各自的利益,你们根本不爱这个地方,你们只爱这个地方的钱。你们为了钱破坏这里,把它搞脏、搞臭,搞得乌烟瘴气。你们背后都有个风景如画、满载回忆的故乡,我们呢?我们柬埔寨人去哪儿?你们达到目的就走,无情无义。”
我还是依然地生活着,义无反抗的煎熬着,我总是觉得比来时的日子好过了,恐惧和失落也渐渐消失,目标也有了,周围都是熟悉的人,让我安心。
也许有一天,我回老家了,选择去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,找一份尽管薪水不高安定的工作,认识个安静的小剩女,结婚,买房,生孩子,工资卡上交,和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、看电视,每周和妻子做爱一次,每月参加孩子家长会两次,每年旅游两次,每年喝吐四五次次。我可能还会长胖,挺着大肚子与人争吵,滑倒在一个洒满夕阳余晖的街头,手里的酱油瓶子打碎了,酱油掺杂着泥土发出阵阵腥味,我迅速站起,环顾四周,拍拍尘土,若无其事地走掉。我还会记木牌?还会记得按摩店牌子下的姑娘吗?我想我会选择遗忘,那时候得我应该追逐着世事的清明,这段故事也就止于唇齿,掩于岁月吧。
微信个人公众号:棺木的诗